交融共生
一百年前的新疆,什么样?
今年年初在新疆住了三个月,大概是近十年来最久的一次。我们向往远方,却总是对身边事物缺乏了解。如同故乡,离得越远,却愈发想要靠近。如同生活,在别处的似乎更有吸引力。
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去了一趟新建的市博物馆。这座城市以曾经浓厚的宗教氛围、高昂物价、极端气候、博格达峰以及游客中转站而闻名全疆,但清朝以前的历史约等于新疆的历史。
因此,对于博物馆的展陈简陋、藏品匮乏,也就没什么好失望了。学到唯一的知识点是,古诗中的轮台县居然在乌鲁木齐市区附近。
唐代诗人岑参两次出使西域,写下《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伊犁境内,四面八方目力所及之处,所有的山峦都属于天山山脉。现在想来,“轮台”也好,“天山”也好,在学习这首诗的中学时代,离我何其之近,却要等到十几年后才知晓它们的真正含义。
也是这时,萌生了多看看新疆历史的想法,恰好看到《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作者欧文·拉铁摩尔是美国人,在中国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中国通。
他在书里写道,“然而我说话已经鲜有北京腔了,而且又转向了天津腔,还掺杂了归化城(呼和浩特旧称)商队口音、甘肃回民口音、维吾尔车夫口音以及边境戍军的口音。”
1926年3月,拉铁摩尔带着仆人摩西(李宝舒)从北京出发,经内蒙进新疆。与妻子埃莉诺·拉铁摩尔在塔城会合后,他们沿着天山山脉由东向西,经木扎尔特冰川下天山,穿越整个南部新疆,翻过喀喇昆仑山口,于1927年9月抵达克什米尔。
这趟一年半的旅途,拉铁摩尔翔实记录了沿途的风景人文,不仅留下文字资料,还附有大量珍贵的老照片,让我们一窥百年前的新疆和新疆人、中国和世界。
拉铁摩尔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商队老板、各级官员、外国侨民、俄罗斯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以及拉达克人,呈现出彼时新疆远超当下的错综复杂。
而这些微观史背后,隐隐可见20世纪20年代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沙俄的覆灭,苏联的建立,使得边境动荡、贸易混乱。虽然新疆尚未被军阀混战波及,但通往内地的商路日渐衰落。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翻译的原因,这本书的措辞和表达方式都非常现代,基本不会有难以理解的内容。另一方面,作为美国人,作者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有独到之处。
然而,书中所描写的是百年前的旧世界,那是旅途全靠马车和雪橇的时代,真正时髦的东西是无线电台,游牧部落还不把国界当回事、过着艰苦却自由的生活,大自然尚未被驯服、被劫掠,天山上的羚羊和野鹿随处可见。
这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感。过去的现实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展示给后人,反而加深了我们与历史的联系。书中写到新疆的很多地点以及一些习俗,我都非常熟悉。或者说,它们近百年并未发生太多改变。而这又是另一种维度的反差。
“乌鲁木齐位于(天山)南北两路之间的最佳节点,是这些被小沙漠、小山脉阻隔的城镇的天然的首府;而整个新疆则被大沙漠、大山脉同世界上其他地方分隔开来,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更难受到外部的影响,所以这个地方几个世纪以来都是闭塞的,变化也更缓慢。”
“新疆不再是一个枢纽,而是人口和商贸流动的终端。输往新疆的还有难以估量的舶来货、艺术、文明。相应的,新疆像进贡一样,向内地输出比较初级的商品,包括原材料、玉石和贵金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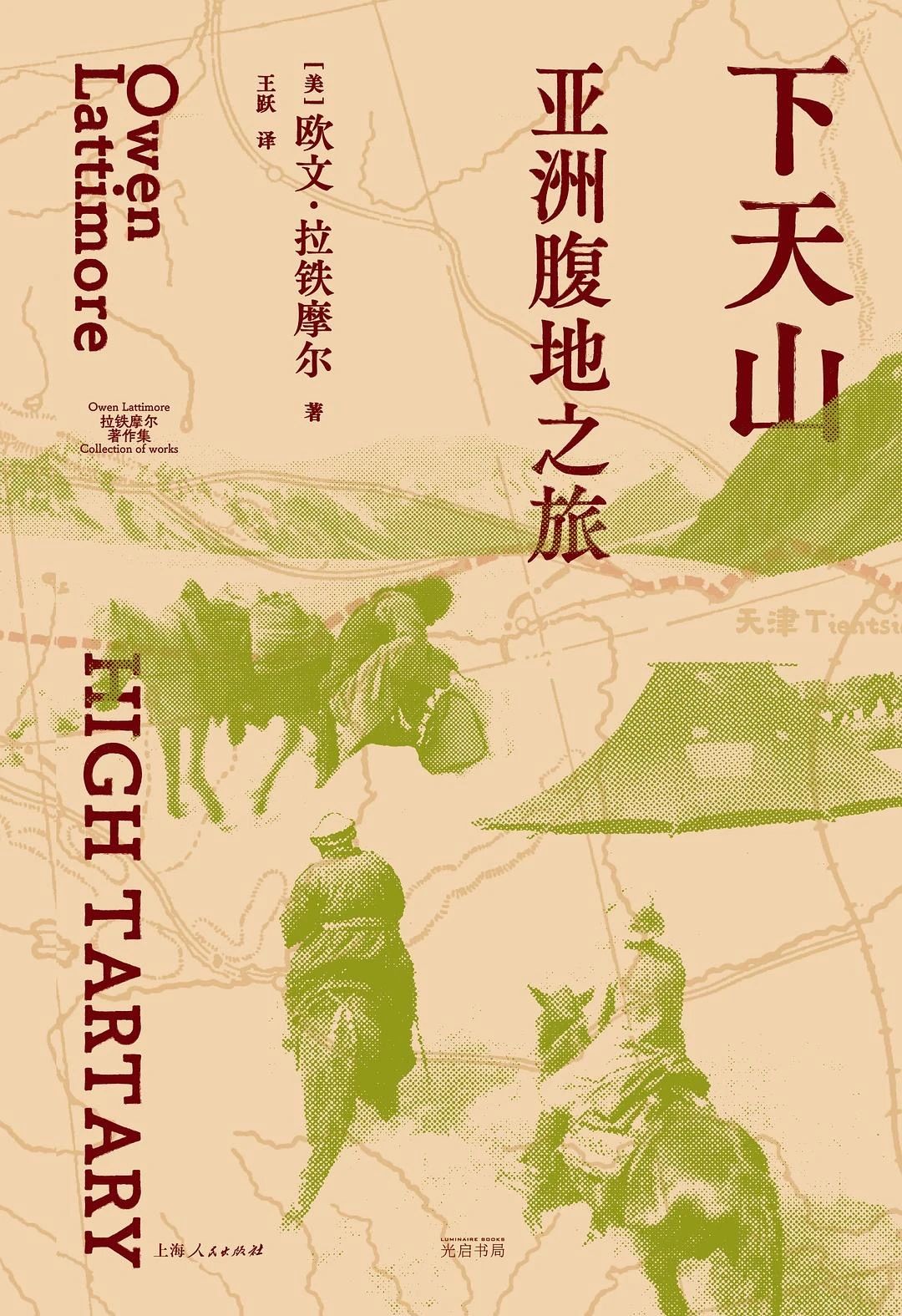
还有一些现在看似“违背常识”的地方,比如说汉人移民。在拉铁摩尔的叙述中,当时新疆到处都有天津人的身影,天津商人、天津车夫、天津戏班子……还有人告诉他,只要能说天津话,在新疆就没什么好怕的。
伊犁河谷是天津人最大的聚集地,“没有什么比伊犁人的‘天津’社群更奇怪的了。在其他地方,他们是一小撮繁荣的商人,在这里,他们是一个完整的社群,从理发师、食品摊贩到富有的商人和地主都有……伊犁就是小杨柳青。”
天津经济发达,是对外贸易的源头,也是新疆原材料运输到内地的出口港。拉铁摩尔从北京到新疆所走的路线,正是商队穿越蒙古的贸易路线。
但是,这跟我从小到大的印象完全不同。在新疆,我认识、听说或者知道来自五湖四海、各个省份的人,唯独没有天津人。不知这些天津社群后来怎么样了,又或者在几代人之后不再记得自己的来路。
可以确定的是,由内地往新疆移民是长久以来的传统。中国人自古安土重迁,但未必没有冒险者和拓荒者,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拉铁摩尔在书中一笔带过,说摩西早年间闯荡南非,在金矿干活,还学会了英语和一些黑人语言。他们行至喀什,有人认出摩西,提及这段过往。得知拉铁摩尔要去边疆旅行,摩西坚持跟随,他说自己喜欢出国,尽管他已是发福了的40岁男人。
关于中国人去南非淘金,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在世界各地招募劳工前往殖民地南非,其中就有华人。后来英帝国崛起,取代了荷兰的地位,也获得了荷兰原有的殖民地。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到20世纪初,大量“契约华工”被输送到世界各地,南非即是其主要目的地之一。
说回《下天山》,大部分内容集中在天山北路,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北疆。或许是北疆汉人更多,官员和外国人也较多,拉铁摩尔有更多交流的机会。而在天山南路,汉人少,能说汉语的维吾尔人也少,没有沟通机会也就缺乏写作素材。
除了内容引人入胜,欧文、埃莉诺包括摩西,对待旅行的勇气和热情也令人敬佩。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欧文和埃莉诺骑马,摩西赶马车拉着行李。他们风餐露宿,在争夺“世界寒极”的塔城和巴里坤经历了严寒的冬天,又在酷暑穿越南疆,由于白天太热,只在夜间赶路,但怎么也避不开肆虐的跳蚤。
埃莉诺应该是当时唯一一个从北京出发、经过新疆到达印度的女性。在行程前半段,她独自从北京到满洲里,再从满洲里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到新西伯利亚,然后沿着铁路支线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城市),最后坐货运雪橇抵达塔城。这段雪橇之旅穿过的茫茫雪原,冬季平均温度比北极还低,埃莉诺不得不在暴风雪中自己驾驶雪橇。
欧文写道:“这段西伯利亚之旅所需的勇气和毅力远比一个男人穿越蒙古所需的勇气和毅力多得多。”
当时的新疆,男女共同出席饭局仍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这些外国人携妻子出席,一些中国人的妻子才得以一起出席,更遑论女性只身旅行。

微信读书有评论说,拉铁摩尔都去了伊犁,感叹风景的文字几乎没有,对自然的感受阈值未免太高。这恐怕有些冤枉作者了。
在翻越喀喇昆仑山口时,拉铁摩尔发出感慨,“这段行程的最后几个小时是我们所走过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路程,我们所经过的山口周围的景色令人惊叹不已。在一条两英尺宽的小路上,我们脚下常常会出现几十英尺深的悬崖或者几百英尺深的陡坡。”
“我发誓,有那么一刻,我的两只脚都悬在半空。我骑着马经过了一些我从不相信能骑马通过的转角。想放弃已经太晚了,甚至从马上跳下来求生的机会都没有。”
也许不是伊犁的风光不够壮丽,而是翻越天山的路途不够艰险,天山上的冰川无法与喀喇昆仑山的冰川相提并论,毕竟后者是“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峰的所在地。
拉铁摩尔的旅程虽然艰苦,但到底还不至于遇到生命危险。比他早三十年前往亚洲腹地探险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历经探险队几乎全军覆没的磨难,九死一生,发现了楼兰古城遗迹。
这也是我对这些旅游文学和探险文学兴趣所在的原因。别提喀喇昆仑山和西藏外喜马拉雅山系,就算是近在家门前的天山,终我一生都很难以这些探险家的方式抵达,于是愈发钦佩他们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从这样艰险的旅途中又能获得什么呢?欧文和埃莉诺著书立说,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专业学者。
“好家伙!”摩西说,“我竟然就到了印度。”
拉铁摩尔提议,等摩西回到天津后可以跟别人讲述这一切。
摩西却说:“谁?在天津,谁会相信这一切?”
在此之前,摩西还说过一句话:“旅行就是旅行。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试试。”
